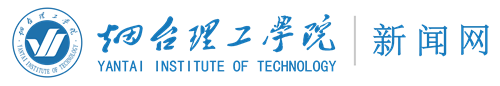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
嫌春天来的太早,蓝天白云下灰色的树枝还一丝不挂,隐隐约约的绿意却散满其中,像电脑合成复制粘贴上去的,太假。我刚说这个角度看外面颜色的搭配像极了冬季富士山的色调,全被这种绿毁了,这个角度再也看不到富士山。
可嫌弃春天的原因总不止这些。
还有春困。
老师在讲些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抬头看天的瞬间眼皮沉起来,晴朗的蓝还没尽数收进眼里黑暗就挡住宇宙成了一场大梦。
我看见自己又和杨柳枝一起坐在了舞蹈室里,倚着墙,面对落地窗耳机听苏打绿。暮春的黄昏被树影切割得斑驳,支离破碎一点点漫上木地板,映在扶手杆上温柔又颓唐。像等待孩子的那个窗口,通过它看到的是白发苍苍,亲切平静却随着无可奈何的时间消逝,再多的慈祥都只是刹那的停靠,暖了心房长了心伤。
十四岁时每到一个周末我和杨柳枝就会翘掉作文班逃到舞蹈教室里,听歌,听苏打绿偶尔也听张悬和杨乃文。苏打绿会唱:“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我转过头去看镜子里的杨柳枝,试图找出我们的相似之处,她垂着脑袋我看不到她的脸,却还是长久地盯着镜子看我们的轮廓。渐渐那些线条越来越模糊陌生,最后整个世界在我面前睡去,我醒过来被抛进另一个梦境。
那是十二岁的夏天。我和杨柳枝骑着自行车滑下一个大大的坡,甚至松开车把任车子东摇西晃往下冲,载着兴奋得大喊大叫的我们。那时候的路总是又平又直没有障碍和行人,只有被我们吵响的蝉鸣和被风吹得欢笑的杨树叶子。路的尽头是飘着消毒水味儿的游泳池,一头扎下去消毒水的味道越来越浓像在医院里。
医生从手术室出来摘下口罩,用略沙哑的嗓音说:“脑溢血……”后面的话我没听到,大人全都扑到医生身边把他包围吞下了他的声音。我坐在长凳上不安地绞着双手,屁股下金属的凉意蔓延到全身,我觉得冬天就要来了。
过几天我见到奶奶,她那样子真像睡着了。我想起她给我念庄周梦蝶的故事,她说蝴蝶那么漂亮,能梦见蝴蝶的人心里一定开满了花。现在我默默对她说,奶奶你这个梦可以做很长时间了,你会变成只蝴蝶也不用担心是不是真的,本来人生就是一场大梦。
凉凉的液体从我脸颊上划过,盈盈水光淹没四周,在潋滟晴方好的游泳池里飞出一只白色的蝴蝶,折射着金色的阳光太刺眼,我不得不闭上眼睛。
等我睁开眼还是和杨柳枝坐在舞蹈室里,耳机里温柔又颓唐的声音在念白:“……身体形式是生命里的各站停靠。”还是温柔又颓唐只是那个窗口再也没有了白发苍苍。我想说梦才是生命里的各站停靠,所有生老病死欢乐趣离别苦都在梦里,无法预测梦就像无法预测下一个站点的意义。可是做梦好累啊,哭哭笑笑消耗掉生命还不想醒来。我还能遇到她吗,还是从此就去往了没有梦的角落,在梦里我还没有变成蝴蝶。“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我从前大概不是一朵花吧也就没有办法寻找我自己了,我内心大概没有开满花吧也就没有办法做梦成蝴蝶了。
老师的粉笔头把我敲醒:“你怎么又睡着了?”
“我……我……”我揉着眼睛站起来,“……觉得这个题选C。”
作者:外2002-1 张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