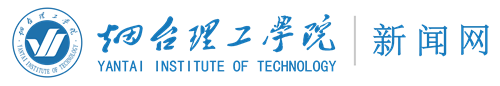我舅妈是个厉害人物。
在她还不是我舅妈的时候有过一次婚约,嫌对方穷,反悔了。按规矩她不能再从当庄找对象,这个时候姥姥看中她了,然后她就成了我舅妈。因为我舅舅长得好看,姥姥找媳妇的唯一标准就成了也要长得好看。
当然在农村女人长得好看几乎就是一种原罪,舅妈一直为大家茶余饭后提供谈资,在我有记忆时她就前后成为货车司机、杂货店老板甚至村支书的姘头,这些话语没人知道真假,就像病毒一样悄悄蔓延了整个村庄,因为上不了台面只能在阴沟的边边角角渗透,顺着污水漂流进江河湖海。
在舅妈和舅舅订婚之后流言就变成了穷姑娘攀高枝的故事。我姥爷有钱,彼时他从地质队里退下来,一月工资抵庄稼汉一年的收入,他算是村里高级的知识分子,然而他的知识不能够被合理地应用,所以他的意见只能处在一个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舅妈父母双亡,她的前二十年以一个混子的形象闻名,年轻姑娘们谈论舅妈时都带着轻蔑和艳羡,她们都是善良淳朴却又愚笨的村妇,嫁一个好人家是她们生活安稳的保障。其实她们都多少上过一点学,知道村庄之外还有世界,但她们对真实世界的概念局限在了一周一次坐城乡公交去的市中心。经历和原生家庭让她们注定不能成为像舅妈一样的女人,而受到的一点现代化教育又让她们对这种女人感到好奇和渴望。
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初,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在村庄里盛行,所以我妈默认自己为这场婚姻最大的受害者。她向我控诉姥姥的偏心,形容姥姥说“偏心到都不知道自己偏心”。她反对这门亲事,可姥姥一句“我们找媳妇关你什么事”把她噎得哑口无言。不过随着时间推移,现在她对于舅妈只剩下了满意。因为有的时候舅妈太能折腾,把姥姥对她的偏爱已经渐渐磨没了,偏爱是和物质成正比的,所以舅妈不会再从她的婆家得到更多好处,好处自然就可以多给我妈了。
但是流言从不会销声匿迹,它在舅舅请喜酒那天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舅舅结婚请喜酒的前一天,我的太姥姥去世了。
太姥姥走得很安静,因为她本来也说不清楚多少话,一直被她的儿子儿媳关在最破旧的西屋里。巧笑倩兮的舅妈见她时一口一个“太婆婆”叫着,给她洗发霉的布鞋和腐臭的被褥。然后太姥姥说以后她的钱一定要留给孙媳妇。
妈妈哭着跟我说:“姥姥那时候意识多清醒啊,但是为什么每次看见你,她都要问一遍你是谁的孩子?她真的不认得你吗?”我不知道太姥姥认不认得我,但我是真的很害怕她,一看到她迈着蹒跚的步子拄着拐从西屋里挪出来我就大哭。太姥姥曾经也说喜欢我,过年会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长了霉点的一百块给我当压岁钱。妈妈说,你收下呀,太姥姥给的,喜庆。等我忸怩地接下钞票,妈妈就把钱从我手里抽走,下一秒我会在水泥地板上看见它。“别捡,”妈妈说,“不知道放了几辈子,脏。”
所以我们家几乎没有得到太姥姥的一分钱,妈妈对此耿耿于怀,扬言舅舅要是敢现在请喜酒她就一头撞死随太姥姥去了。我姥姥说:“你撞啊撞死啊,还是那句话,我们家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管。”于是太姥姥的葬礼办在了喜酒之后。舅妈才是真正的“烈女”,她一听太姥姥去世了,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对准了自己的脖子,哭得撕心裂肺声泪俱下:“请喜酒要是敢延了,我就让这把刀溅上血!”姥姥第一个乖乖心肝儿地叫着,哄着舅妈把刀拿走。姥爷坐在一边直咽气,据说他的高血压就是那时候种下的。
舅妈就用太姥姥给她留下的钱请了喜酒,那天她穿金戴银光彩照人,笑盈盈地给每个人敬酒,来的客都送烟送糖。流言一开始吹的是“穷姑娘攀了高枝以后有好日子过了”,等喜酒快结束人们意兴阑珊的时候,称病而缺席的妈妈脸色苍白形容枯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然后她开始哭去世了的太姥姥,声泪俱下让人无不动容。宾客们渐渐聚成一团嘁嘁喳喳,流言四起形成龙卷风席卷了这场喜酒,留下一桌桌的残羹剩饭。姥姥气得冲到妈妈身边用脚踹她,可是妈妈终于坚强起来,跪坐在地上巍然不动。舅妈的微笑凝固在脸上,粉饰过的白脸涨得通红,一定是流言把她吹发烧了。
但是她也扑通一声跪下,和妈妈一起哭太姥姥。她哭,姥姥啊你现在走了,你生前最不忍看我受委屈受累,等我请完喜酒真的嫁给了你外孙,我才能光明正大以一家人的身份给你上香磕头哇,姥姥你在天有灵,知道我早请喜酒是想名正言顺地孝顺您啊。我妈妈噤了声,舅妈的嚎啕就在厅堂里盘旋徘徊久久不散,她哭完太姥姥,就开始哭她自己自幼悲凉的身世,最后用哭腔暗戳戳指责她的姑子婆婆。本家的几个辈分大的女人把她扶起来,舅妈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用眼泪成功博得许多人的怜悯。人们也成功地知晓太姥姥已经去世,喜酒最后不欢而散。宾客走后,姥姥用扫帚把直挺挺跪着的我妈打到在地上,她没有叫出声,任凭姥姥的扫帚有节奏地一下一下抽在身上。姥爷瘫坐在竹摇椅上,几次想站起来都没有做到,反而将自己弄得气喘不顺,只好一边咳嗽一边用拳头捶着胸口给自己顺气。穿着嫣红旗袍的舅妈坐在椅子上只是哭,眼泪从抹白了的脸上劈出纵横的沟壑。我蹲在地上烦躁地用扫帚掉下的竹条划来划去,仰头就看见舅妈脖子上的肉委屈地挤在旗袍的高领里,于是就很轻易想象到了她年老时脸上的皱纹和松弛的赘肉是什么样子。
太姥姥走的时候九十六岁,葬礼就按“喜丧”来办。舅妈作为新嫁娘不肯脱下那身红旗袍,在花圈白幡纸马中间穿梭,白布条象征性把头发挽起,招待前不久刚刚来喝过喜酒的人们。临近中午舅妈披上了孝袍,第一个冲在太姥姥的灵前哭,比方才的女戏子还声嘶力竭肝肠寸断,而且她哭得很好听,声调就像“梁兄啊英台若是女红妆——”我缩在姥爷身后,感觉到他身体在剧烈颤抖。我又往更后方退,看见舅妈孝袍里面的红色若隐若现。这时人群喧哗起来,我听见杂乱的脚步声和妈妈的吼叫,往近处看见姥爷躺倒在了地上,脑壳后缓缓流出若隐若现的红色。“老王家媳妇把他气出心脏病。”
由于姥姥对舅妈的处处维护,舅妈最终占据了姥姥家的主导权。而我们一家已经搬去她们认知的世界中心,很少与舅舅们往来联系了。
我十七岁考上大学,妈妈说应该请她娘家人喝喜酒了。
姥爷的病一直不见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因为意识清醒就显得笨拙的肢体更加无奈,但知识分子向来有骨气,所以他不肯坐轮椅甚至拄拐。在妈妈对于姥爷如何赶来而忧心忡忡时,笑吟吟的舅妈打来电话,说她已经把姥爷姥姥带到了城里,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她在前几年就已经考了驾照买了车。姥姥常说舅妈才像她的亲女儿,妈妈和舅舅太小家子气上不了台面撑不起大局。可是妈妈和舅舅的性格才是因为她的影响,正是她的强势让妈妈没有必要也去做女强人,让舅舅必须也与强势的女人结合如同找另一个妈。
酒席上我一直强颜欢笑,给熟悉或陌生的长辈敬酒。但主场是舅妈的,她的红裙子飞舞在酒瓶菜肴桌椅中,好像考学的人是她一样。她也的确适合作为人群的中心,她的红色衣服很多,人多时她就穿红衣服,显眼又热烈。她就是红色的,泼泼洒洒一整片,风一吹就分散在各个角落,哪里都有她,哪里都是她。突然我听到妈妈叫我,让我坐在姥爷旁边。我走过去,发现舅妈竟起头闹着让姥爷喝酒。我说,姥爷三高有心脏病,喝不了。舅妈翻着白眼,脖子后缩(那些肉又很委屈地挤在一起),她说,小孩子别掺和了,你的喜事,你姥爷喝杯喜酒怎么了?说着把酒往姥爷嘴边送。姥姥也没有阻止,只是看着舅妈笑。姥爷红光满面,咧开不剩几颗牙的嘴冲我笑起来,然后接过舅妈手里的酒杯一饮而尽。
几秒钟后姥爷就倒下了,额角磕在凳子腿上,红色缓缓流出,染红了一大片地毯。包间一片混乱,被撞倒的椅子又绊倒了很多人,打碎的碟子盘子碎片溅了一地,尖叫声不绝于耳。
妈妈走到我身边却出奇的平静,她说,或许喜酒之后我们又要办葬礼了。
外2002-1 张温馨